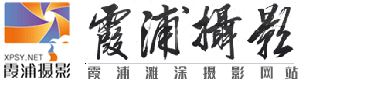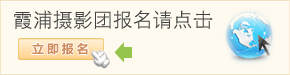霞浦竹江的民俗与风景




童年记忆中的竹江 作者:末摘花
一个人一生可以住很多地方,但他的童年,一定要在一个小村子里度过,这样,故乡所有的记忆会完好地盛放在那里面,当他多年后追忆往昔时,会浮现出一个温暖的场景来。
我的童年是在沙江镇竹江村度过的。那里有我的外公外婆,那里是我快乐的最初发源地。
一、“浮地”之奇风异事
竹江是个孤岛,又称竹屿,位处东吾洋西北海中,四面环海,以岛上产竹,四周临水而名,老早就享有“小台湾”的美名。听老辈说,这个小岛虽然面积不足0.106平方公里,却是一块宝地和福地,当地人代代称之“浮地”。因为,涨潮时小岛便浮起来,落潮时候小岛便落下去,每年夏季的亚热带台风,几乎不会造成海水灌岛的场景。事实也印证了这个传说:竹屿岛经历了历史上历次台风,大潮,临海的房子和街道从来未被凶猛的海水浸漫过。这是它的一奇。
关于这个小岛,还有另一则美丽的传说:竹江是个“老虎地”。它的地形还真像只老虎呢:据说从竹江岛西面,东吾洋西岸的水潮村、小马村、梅洋村等地往东面看竹江岛,整个竹江岛就像只老虎卧江。海水退潮后,岛上露出的一条弧形沙堤简直就是老虎骄傲的尾巴。要是转到三个村背后的目莲寺山上观看东面的竹江岛,那更像一只虎了。若是从海对面的沙江望过去,呈不规则长方形耸起在海中的小岛也像一只卧虎--胖乎乎的村头就像虎头,瘦下去的村尾就像虎尾,中间粗粗壮壮活像老虎的身子。后山上有一个山岗叫老虎岗,山岗上长满绿油油的小竹子,像极了毛绒绒的虎毛,海风一吹便一波一波地飘动着,很是漂亮。
竹江岛分为前澳与后湾,南宋时张、郑、陈等姓氏相继迁此定居,小小的村子里左邻右舍都是沾亲带故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回到村里,走在窄长的青石巷子里,还会有村人不时亲热的唤我一声“阿表妹”。岛上的人历代信仰妈祖,一前一后建有两座马祖庙,叫前澳宫与后湾宫,其历史悠久,建筑风格各异。每年农历三月二十至二十六日是竹江村纪念马祖神节活动日,两宫都请戏班演戏、祭神、迎神,是岛上一年里最隆重的节日。这几天,村子比过年还要热闹:出嫁的女儿被请回娘家来看“阿婆走水”;在外做事的汉子们赶回岛上,带着老婆孩子回来参加盛事。当地人有一种说法,妈祖走水时从来不会下大雨。遇雨,天会晴;遇大太阳天,又会下点雨调剂一下。去年,我也回去看神节,临行的一个晚上大雨如注,晨起到了竹江还一直下着小雨,可是到了妈祖走水活动一开始,雨就停了,滴雨未落,活动结束,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似乎在轻轻述说着什么。这是第二奇。
霞浦民间有一句俗话说,“竹屿留人客,伞在门兜角”,意即半心假意。这实在是冤枉竹江人了。下岛需坐渡船,潮水不等人,每次过渡搭船都是客满了马上就走,不然,不是渡船走了没船可坐,就是海水退潮无路可回。主人们只好一边嘴里挽留客人,一边怕客人赶不上渡船误了事,提醒客人带上雨伞,出门坐船。
200多年前,竹江村的前辈们为了让子孙生活方便,在村中间的海面铺上一条七里许的石板踏路,连接陆地与竹江岛,通往西岸的小马村,这就是著名的竹江汐路。桥为东西走向,因建在海泥上,故得名。据查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海中古代石桥,这是第三奇。
县志记载,此桥为清乾隆年间由乡绅郑绣轩倡建,至嘉庆十六年(1811)郑启昂耗巨资建三年而成,后被潮水冲垮,其子郑琼森又进行三次大修才得畅通。由于地处海涂泥泞中,建路时,路基用松树打桩、铺垫杂木草皮,然后铺上条石横竖三层砌成。全长3651米,最宽1.8米,途经六座桥,最高2.9米,其中有四座桥,桥孔上下二层,边有小孔,具有排潮防潮作用,是目前国内罕见的海埕石路桥建筑。如今已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并有专人养护。潮水退后,村子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它了。妈妈说,小时候,我要去嫁到梅洋村的姨妈家,都是大人挑着竹篮子,一头坐着我,一头放着我的衣物和外公送给姨妈的鲜货。
岛中有远近闻名的两口井,就在离我外婆家不远的学堂宫附近。井分上、下两口,久旱不涸。两井并排,相距不过一米多。扔一块小石头进去,上井响锣声,下井响鼓声,故得名。这是第四奇。凡初次到这个岛上来的人,多被领到锣鼓井瞧新鲜。村人说每年必掏井三四次,因为里头的石头太多了。我小时候,没少往里面扔石头,当然,都是瞒着大人偷偷扔的。而今想起来,那种兴致勃勃,乐此不彼的劲头也随着童年的逝去而如云彩飞过了。
二、时光深处海腥味芬芳萦绕
说起竹江,不能绕过去的一笔是海鲜。竹屿岛依傍有“蓝色明珠”之称的东吾洋,海产丰富自不必说,且因了旧时海水污染少,交通运输不发达,海产品更是臭贱到满坑满谷。除了马鲛鱼,白鳓鱼,海蛎,海带,鲶肉等,更有滩涂上的跳鱼、章鱼、螃蟹、鲟等。岛上人家,一年四季顿顿海鲜不断,无海鲜不欢。记得小时候,外公打发我去小店打酱油,从来都是给我5分钱,一只瓶子:酱油打3分钱,醋打2分钱,混装着提回家。烧鱼怎能离得开酱油和醋?家家户户都是这样酱油、醋一起打来,烧鱼时一倒了事。
受潮汐影响,竹屿岛四周涨潮时的一片汪洋,退潮时会露出洋底一半多的泥土滩涂。辽阔的浅海滩涂上盛产章鱼、跳鱼、土鳝、鲟,青鳗。外公的几兄弟最擅长到滩涂“下土”,即讨小海,是捕土鲜鳝和章鱼的能手。他们架着滑板在滩涂上穿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孤线,不时停下,俯身,一个半天就能收获一竹兜的“土头货”。鲜章鱼自家吃不完,外婆就把它们浸到装着鲶露的小坛子里,浸到一坛满满的时候,送到南屏村,给她的娘舅吃。娘舅则把自己做的米糖,种的大米、京豆回送给我们。捕来的鲟,岛上的人用人草一只只串起来,三五个小串串起一个大串,拎着到城里送亲友。夏天的螃蟹一土箕一土箕的,倒进大鼎里煮得红红的,熟透了,并不急着捞起,而是把柴灶的柴片灭了明火,让余下红炭慢慢把锅里的螃蟹一只只煎到不出水了,才捡进大大的竹编吊篮里,摊开来,挂在椽下晾着。吃饭的时候,取下吊蓝拿出几只来。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竹屿人家谁没有几个大大的吊篮?每年三月末至六月初,是官井洋捕鱼季节,村中五十余艘船,同时开赴,气势颇为壮观。捕马鲛鱼从渔船系縺时起,就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女人统统回避,一切由纯爷们自行操持。为祈求平安丰盈,每船都得尊阿婆香袋或软身神,随备香灯元宝,随时供奉。渔船一般下午三四点钟出海,先在近海“洋头里”捕三天,然后去官井洋十天或半月。那个时节,沙江人讨黄瓜鱼,竹屿人捕马鲛鱼,各得其所。因着黄灿灿的黄瓜鱼,银闪闪的马鲛鱼,官井洋内有沙江人“金一缸,竹屿人“银一缸”的美丽说辞,“金沙洽,银竹屿”也由此而来。
马鲛船归航,马鲛鱼在海塘堆砌成山,熠熠发光,好像一座座小小的雪山,整个村子里弥漫着一股鱼腥好闻的气味。马鲛鱼籽用盐重重的腌了,挂起来晾干,干透之后就是送亲友的好东西了。小时候我老觉得晾干之后一块一块椭圆形的马鲛鱼籽像极了大人的鞋底,大的像42码的鞋底,小的也有38码的鞋底那么大。岛上人习惯把一尾一尾新鲜的马鲛鱼尾巴用绳子系成串,送人好有型。
提到竹屿的海鲜,也有一笔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竹屿的竺蛎,也称竹蛎。 由于地理的原因,竹屿岛周边海水浅,退潮时大面积的海滩裸露出来,受到大幅度的光曝晒,吸收充足阳光的海蛎就更为甘甜肥美--这是竹屿海蛎以品质佳,口感好蜚声省内的原因之一。
竹屿的海蛎品质佳,口感好,除了得天独厚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竺蛎的养殖方法是:农历三四月将竹子扦插到海里,让它长柒头,到七八月收起来刮去柒头,留下柒座,然后送到溪南青山、长春武岐、门岐一带育苗,让海蛎种子附上竹子的柒座上面,再运回来插到海里长出海蛎。育苗这个步骤有点像借种怀胎,是竹屿海蛎质高量多的一个关键,也是竹屿人在长期的海水养殖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回溯历史,海蛎的最早原始养殖方式主要以投石养蛎,收效甚微。竺竹生蛎,仅百余年。民国版的《霞浦县志》记载:“蛎为南区特产,涵江、沙江、竹屿、武岐居民,以蛎为业,始于明成化间(1465-1487年)。明郑鸿途《蛎蜅考》云:“福宁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籍海为活……独竹屿孤岛,无田可耕,无山可垦。宣顺前,渔箔为生,成弘后,箔废而蛎业兴,肇自先民,取深水牡蛎之壳,布之沙泥,天时和暖,水花孕结,而蛎生壳中。次年取所生残壳而遍布之,利稍蕃。然蛎产多鲜,巨鱼逐鲜,馋食无厌,众心胥戚,取石块团围,稍无害。但石块不过三、五,波浪风倾,害复如前。乃聚议扈以竹枝,水中摇动,鱼惊不入。哀我人斯百计经营,幸天不爱道,地不爱宝,竹枝生蛎。乡人郑姓者,随斫竹三尺许,植之泥中,其年丛生蛎,比前更蕃,团名曰竺。以竹三尺,故名也。乡人转相慕效,蛎遂传。沙洽亦然。蚶澳,洪江、厚首等处,耕种之民,踵武遍植,以为余利。”
从这里可知,竺蛎技术原是聪明智慧的竹屿郑家人发明,而《蛎蜅考》则作为我国首部系统介绍海蛎养殖的著作载入中国海蛎养殖史--若不是这次写这篇童年记忆,只知道吃竺蛎的我,哪里懂得,勤劳坚韧的孤岛先民,为求生计,谋发展,曾经为中国海洋养殖史,写下过这样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一月开始下海讨竹蛎,一般收到正月底就结束了。为了能多赚点钱,一部分人运着带壳的海蛎从水路去赛岐、福安、宁德、福州一带卖,也有一部分人一路上边开边卖,俗称“开蛎仔”。多数的海蛎是现开现卖。妈妈说,外公年轻的时候,常常挑着两大浅篮外婆开好的海蛎,一早从小马村的后门山经马洋走到城里卖,卖完再走路回家,一个来回就是80里路。卖不完的海蛎煮熟晒干,售之岛外。据载:因品质上乘,迨清光绪年,闽之兴化、永春诸地,及南洋客纷纷前来买蛎干,故蛎户集股,以晒蛎为业,自是虽多扦亦无馁患,居民利之。至民国,福州南台设有蛎干牙,现福州市台江区解放大桥至闽江大桥之间为旧时南道码头,老福州人还称之为“霞浦蛎蜅坞”。 每到海蛎收成季节,竹屿人照例要分送二三次开好的海蛎肉给亲戚朋友。一般在收成之初送一次,中间一次,季尾一次。用大小不一的木桶一桶一桶地装着,木桶汪着一层清清的蛎水,在上面放一小片长方形的小红纸进去,就是一份好礼了。每到这个时节,在城里工作的妈妈,就会享用到她娘家人送给她的原装新鲜海蛎肉。老妈总是大碗小碗盛着分送邻居、朋友,在她的朋友圈里,没有不尝过竹屿海蛎的,也没有不交口称赞的。连她的外地同事,从不爱沾海鲜的,吃过竹屿海蛎也要大呼好吃,从此爱上那一口。
海蛎的吃法很多,岛上的人最常见的一种吃法就是用白水煮,厚厚的撒一把盐进去,吃好多天都不会变味。也许是小时候吃惯了,到现在,这种最简单的清煮还是我的最爱。还有炒蛋,清炒,跟酒糟一起煮,跟炒熟的黄豆一起腌。。。海蛎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运输又不方便,于是晒海蛎干,闲时再销往福州等地。海蛎要煮熟了才能生晒成干品,大锅大锅煮海蛎的汤水可是个宝,可以熬成海蛎油,用瓮装着一吃就是一年。海蛎油可是当时上乘的佐料,吃法很多:拌青菜、煮米粉、沾海蜇皮。。。都很美味。海蛎还有一种费功夫的做法,就是炸成海蛎饼,也就是“蒲蛎包”。把海蛎裹上磨好的米浆,柴炉大鼎,烧烧热的油锅里炸熟,外脆里嫩,香气四溢,时人已经很难吃到这样的美食了。但我小时候是不吃的,往往是看到一块块比小碗还大的“蒲蛎包”就想哭,实在是吃腻了呀。父母亲知道我们一次吃不下一整块蛎饼,迁就我们,切成四份,一顿吃不完,下顿用油煎了再码上盘子给我们吃,我们的筷子从不往那个盘子里伸,父母亲恨虽恨,也拿我们没办法。
旧时竹屿岛只有一条青石铺就的小街,岛民的房子沿街两边一字排开,一边是临海的,一边是靠山的。每到开海蛎的季节,家家都在门前用木板搭起一个像桌子一样的架子,搬几张木头矮凳子出来,一家老的小的围坐在一起开海蛎,这样的场景在开海蛎的时节,随处可见。开海蛎前,大们会用布条把左手的五个手指头厚厚的缠起来,扎紧,以保护手指头不会被蛎壳划破。开海蛎的工具很像一把螺丝刀。开海蛎壳的要领是左手五指捏着未开壳的海蛎,刀尖朝着蛎蜅嘴缝一撬,所谓手起刀落,持刀的右手腕一转,一抠立马就可以将蛎肉刮出。竹屿的男女老少,个个都是开海蛎的能手,往往一边招呼客人和家教子女,一边手里飞动着,不一会儿,面前开出来的鲜蛎肉就盛了一碗。
大人不让我开海蛎,却管不了我学着大人的样子缠指头。把外婆留下的碎布条一条条拿出来,在手指头上缠紧,却扎不起来。于是便拆了再缠,缠了再拆,一个人坐在屋前的石阶上做得津津有味--儿时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三、柔软如丝的旧时生活记忆
据县志记载,清道光间赠奉政大夫的张光孝有《竹江十景咏》:“渔村神会、蛎市估船,虎头远眺、石桥晚归、榕坪消暑、大门帆影、沆尾橹声、夏夜渔灯、秋江蟹舍”。但是小时的我,并不懂得欣赏竹屿岛的美,当时我最爱去的地方,是海塘。
所谓海塘,是沿海边的人家在房前筑起一块地,户户相连成一片空阔的场地,从家门口一直通到海岸边。海塘一般都很大,很多生产作业都在这里操作:补渔网,晒渔网,寒冬腊月夹海带苗子,平时晒海蛎干、海带干,熬鲶露。。。一年四季,一走到海塘,海的气息就迎面扑来,里面还夹杂着各种海鲜好闻的味道, 如果说童年是有味道的,我的童年就是海腥浓重的味道。
冬季海蛎从海上收上来,外婆和村子里的老人孩子就坐在海塘上搭好的海蛎架上开海蛎,挣工钱,嘴里聊着家长里短,手上你追我赶比着快,这时候的海塘,又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笑语喧哗。肥胖的海蛎肉里边偶有寄生的小小螃蟹,最大的还没有黄豆般大小,但清甜美味,是我这个“城里的外甥女”专享食品。外婆总是用另外的小酒盅装着,留着等我玩累时跑到她身边再给我吃--那是我小时候吃得最甘美的零食了。 农历三月是捕马鲛鱼的好时节,捕马鲛鱼的船儿归来后,船上的渔网拖到海塘上晒,一杆一杆地挂起来,把整个海塘挂的像银幕一样, 阳光下一片片闪闪发亮,我们在网下跑来跑去玩捉迷藏,打来闹去,全不管大人东喝一声西吼一嗓。
夏天的夜晚 ,夜幕降临,暑热消散,大人们把家里的竹床搬到海塘上,横七竖八地排开,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躺在丝丝冰凉的老竹床上纳凉,手里摇着蒲扇,这是各种故事纷纷登场的时刻:田螺姑娘,财主,秀才 ,曹操,刘备……我最爱听又最怕听的故事自然是鬼故事,既盼着他们开讲,又很想迷糊过去不要听见。山妖的故事最是记忆深刻:说是某天有一个人走在山路上,突然白光一闪,这人就跟着消失了--他是被山妖闪掳而去的。家里人苦苦遍寻不得,几个月后人却自己回来了,但像换了个人似的,蓬头垢面,半痴半傻,头脑空白……这个人是哪个村的叫什么人氏谁家的儿子或老子,每次都说的有枝有叶,煞有介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世界里,没有比山妖更可怕的了,以至于整个童年我都害怕一个人走路,处处时时提防着山妖……海风浩荡,没有蚊子,好凉爽的夜晚啊,躺在外公的胳肢窝下,先是眼皮睁不开,然后觉得大人们讲话的声音都远了远了,我努力支楞起耳朵,还是不由自主地睡了过去………
白天潮水退了 ,一大帮熊孩子们就沿着海塘边的石梯下到海滩。堤岸的岩石上爬着好多的“船鹤”,也就是船蟑螂,我们每走一步,它们都大惊失色,慌不择路--小小的征服欲往往在这里得到大大的满足。于是,小伙伴们常常带着吃水果罐头空下的玻璃罐,在海滩上捉船蟑螂,捉小螃蟹,赶着它们四处跳窜,还捡小贝壳、小石头,泥一身、土一身的回家挨骂。那时候,海产丰富,退潮的海滩上有时候会爬着大大的鲎和浮着降落伞一样白色的海蜇,大人们对自投罗网的它们熟视无睹,因为实在是太常见了吧。
我也曾跟着大人们在海塘边等待归来的渔船。捕渔船在海浪的托举下醉汉似的摇摇晃晃慢慢靠近海塘,船上那个归家的人露出白灿灿的牙齿笑着,这是我百看不厌的场景之一。记忆深刻的一次伤心等待是捕马鲛鱼的船靠港了,船上我的表舅表哥们把我身边的男孩子们一个个接到船上,说是去吃用米汤煮的马鲛鱼饭,而我是一个女孩子,是绝对不能上船的,让渔船沾了秽气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我最初的性别意识,应该始自那天吧。:)
孤岛竹屿还有一样出名的,就是缺水。因其四面环海,淡水匮乏,岛内锣鼓井的水含碱量高,烧水,上面浮一层淡黄的油;洗衣服,久之衣服偏黄;做饭,稀饭上凝一层带铁锈黄的米汤,有点苦有点涩。霞浦民间有一句说人脾气臭的话就是拿竹屿人说事的,即“竹屿人,咸水洗脸。”意即咸水洗脸的人跟别人不一样,性情硬。其实,竹屿人不唯用咸水洗脸,生活中除了喝的水,其它一切都用咸水。唯一一个可以用来烧水饮用的是码头附近一个小小的“岐窟”。山间一壑,有泉滴一点一滴日夜不绝,村人用甘叶引入下面一小窟中,以瓢舀到桶里,或以甘叶直接引入木桶,提回家烧水喝。水质清澈,甘甜。因为泉眼极小,“岐窟”边上常年摆放着排队取水的大小各异的木桶,日夜轮流不息。岛人从来依先来后到而取,从未听说有人因取水而起争执。
因为缺水,岛上的女人们结伴去邻近的小马村、水潮村的溪边洗衣服是常有的事,听妈妈说,我家堂舅妈有一年跟岛上两个女人结伴去小马洗衣服,挑着洗好的一担衣服从“踏路”走回家,误算了潮水,走到半路,潮汐涌来,三人被卷裹着随波逐流,万分危急之下,幸有梅洋村的老汉在滩涂吊跳鱼,及时施以援手救下,三女无以报答救命之恩,遂拜老汉为义父,一时在远近传为美谈。后来,竹屿人开始开船到沿海各地运水解决用水困难,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海底铺设管道,从梅洋赤溪引进水源,岛人彻底结束“咸水洗脸”的生活。
夏天榕坪下和小伙伴们捡拾小榕叶卷起来吹口哨,蝉鸣如瀑倾泻下来;入夜的星光满天,渔火点点;一汤一匙喂我长大,教会我“月娘月娘,小儿无知,耳朵还我,剃刀给你。”等等好多童谣的外婆……竹屿岛上,生活简朴,人情温暖。何况,通往外婆家的路,在多数人记忆中,总是一条温情的小路。只是我童年的竹屿岛已经跟童年的岁月一起远去,曾经把我驮在肩膀上走“踏路”、划着小舢板带我去海上兜风的我的阿表哥们,而今他们古铜色的脸上都沟壑纵横了。年岁增长,我也慢慢懂得,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是可以恒久远,永流传的。小有慰藉的是我还可以在今天用自己的笔为竹屿岛留下微光浅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