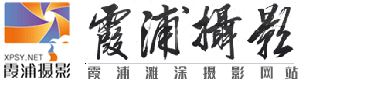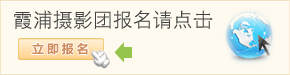建善寺里的银杏树
寺里的银杏树,在冬至前后,大概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会为自己换装。葱绿了一个夏季的银杏,失去了叶绿素,要过冬了,只好让叶子凋零。但银杏叶子却把自己生命的尽头推向极致。如果不去细想时间的流逝节奏,而把它想象成一个即景,那么我更愿意将银杏树譬喻为一位新嫁娘或者魔术师,抖一抖日常素朴的绿衣裳,一转身,就成了一树金黄的盛装。如果用慢镜头,我们忽略的就是关于情感及心理的因素了,比如新娘临嫁前的依依惜别和娇羞,或者魔术师欲盖弥彰的假作真时的布景。

其实,时光的脚步是渐缓的,特别是心里充满期待的时候。每一天,你都可以在阳光下,秋风里,看到数枚绿叶慢慢变成金黄。绿黄相间的比例不断变换,就象在画板上不停地涂抹颜色。叶落归根,这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但不意味着走得就要决绝和彻底,还有留恋和等待,就象一出戏,等到高潮过后,主要人物的宿命才逐渐清晰起来。

我为银杏树而来,与好友老肖在寺里邂逅相遇,以为他与我怀揣同样的目的。在这样的季节里,除了银杏,谁会隔三岔五地往寺院里跑?可老肖眼中是银杏树下曾经的那座大雄宝殿。殿宇已经荡然无存,前不久,一个风狂雨骤的夜里,早已年久失修,并为白蚁噬空的木质构架,终于不堪重负,轰然坍塌。老肖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建筑而数次来到寺院,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没有实物可作凭依,老肖依然说得神彩飞扬,可见他对古老建筑充满了怎样深厚的感情。他虽然是学建筑的,但并没有用自己的专业术语与我对话。他的目的很明确,只是想用镜头记录下殿宇的重建过程,包括一砖一瓦、一石一木,也包括那些仿旧的飞檐斗拱、藻井彩绘,都要保存下真实的影像。早些时候,他“修旧如旧”的建言未被采纳,如今已成泡影。由于他的关注,重建时会利用旧寺遗存下来的柱础、石碑、断垣,新寺也会建得更气派、更巍峨、更现代。可我在老肖的眼神中还是读出些许的怅然若失。是啊!新建筑可能还依稀有旧时模样,却只是过往的残存影子,影子不是废墟,不足以思古与凭吊,至多算是记忆中的惊鸿一瞥,在这个层面上,残存又有什么意义呢?

银杏树少了殿宇的依傍,显得有些孤清。没有近物的反衬,也就没有那些牵牵扯扯,枝枝蔓蔓,倒成就了银杏心无旁鹜的告别演出。

银杏一枚一枚黄了,又不随时掉落,要等到缀满一树金黄,才拉开演出的帷幕。象似在眷恋离别时的美丽,却又不让最后的美丽萎顿如尘,每一枚叶子都是完整轻逸的,并没有因淹留过久而让风雨侵蚀得残损枯黄。这让最后的大限来临,不是“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空无,而是充满留恋的温情。每一枚树叶的离去,不是直坠的凋零,而是回旋的飘落,一步一回首,蝴蝶飞舞般优美地完成。

银杏每年飘落,承接落叶的除了空阔的庭院,还有斜挑的檐角。此时此地,树下的古旧殿宇已经拆除,那一路相依相伴的故事还会延续吗?寺院初名“建福斋”,原建于旧温麻县治所,公元711年,随县城迁徙到县邑,在此落地生根,并改称“建善寺”。之后,在千年的沧桑里,几次重建,几番扩建。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已末年(1563年),倭寇侵州城,县令徐甫宰恐寺为倭营及其蹂躏,不得已而令军民举焚之。”一位县令不能守住一方城土,抱着“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心态,一把火将寺烧了。史籍趋炎附世,为之避讳,说是不得已,是现实的吊诡还是历史的反讽?实在让人嘘唏。

之所以翻这段历史,是由于千年古刹的缘故。我想看看能见证寺院千年时光的会是什么。肯定不会是寺院了,因为火烧四年后,寺院重建,遥远点乐观些说,让寺院一路平安,不再重修,保存至今,也就四百多年。我倒想是这棵银杏树,不是已长成参天大树,一直生生不息吗?可书上也只说是百年银杏,就算要质疑,可还有年轮在,而且在大火之中,银杏树就能幸免吗?事物有了时间的厚度,就相应地蒙覆上历史的尘埃,时间的长河里,不要说最初的样子不真切,就是继续前行的脉络也会扑朔迷离。穿过历史幽深漫长的甬道,人、物、事件很难全身而退,留下的可能只是断简残碑、废墟遗址、零星的文字和片断的记忆。

老肖告诉我,寺前原有两株银杏树,一左一右,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株倒了,不知去了哪里,可能成了建筑材料,也可能化为一堆柴火。无知觉的建筑不能见证时光的流逝,有生命的树也不行。天地悠悠,惟有时间无处不在的虚无。

一位寺僧从庭院静静走过,要走上台阶时,停了下来,抬头望着还是满树金黄的银杏,拂去落在头上肩上的银杏叶子,神情安详肃穆。在整个季节里,寺院任由落叶满地,从不清扫。或许,在心里,每年一场银杏的飘飘落落,已足以见证寺院的久远了吧!
文中图片由爱尚坛友龙泉、迷途知返、寂寞海、龙首芯、风萧萧提供。
来源于爱尚霞浦